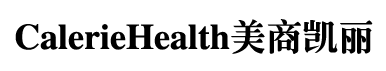一旦你清楚要什么,宇宙就会帮你实现!

生命,是很奇怪的。
一旦你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,许多事情就会发生。生命会通过一个朋友、亲戚、老师、一位老奶奶或其他人来帮你如愿以偿。但是如果你害怕尝试,只因为父亲可能把你赶出家门,那么你就迷失了。
生命永远不会帮助那些因为恐惧而屈服于别人要求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说“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,我要去追求”,那么有些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在过程中,你也许必须挨饿,挣扎过关,但是你终将是个有价值的人,而不只是个模仿者,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。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害怕特立独行,我知道这对年轻人尤其困难,因为印度这个国家不同于美国及欧洲,在这里是没有经济自由的。你说:“我如果不听从,我会怎么样?”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,你会碰到一些事或一些人来帮助你。如果你真的敢不同于流俗,你就是独立的人,生命就会如愿。你知道,在生物学上有个现象叫“变种”,指的是从自己的种类中突然地自发脱轨。如果你有个花园,种了特殊品种的花,有一天早上,你可能会发现其中竟长出全新品种的花来。这个新长出来的东西就叫“变种”。因为它是新种,所以很突出,园丁对它也特别有兴趣。生命也是如此。一旦你开始冒险,你的心及你的周遭就会发生变化,生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给你助力。
你也许不喜欢它出现的形式,那可能是悲惨、挣扎与饥饿,但是一旦你能迎接生命,事情就会水到渠成。可是你瞧,我们并不想迎接生命,我们老喜欢玩安全的游戏;然而那些玩安全游戏的人,也死得非常安全,不是吗?
首要的事情,是彻底清空心中已知的一切;
其次,要有一种没有指向、未被控制的能量;
再次,还需要最高形式的秩序,秩序在这里的含义,是彻底终结冲突带来的混乱,是没有任何特性的心灵所具有的一种品质。我们必须把借助方法的想法和做法彻底抛弃。
核心问题是,心灵——包括内心、大脑和整个物质有机体——能否没有任何扭曲、没有任何强迫因而毫不费力地活着。
请问问自己这个问题,这一切就是冥想。我们的心灵是扭曲的;
它被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,被宗教、经济结构和被我们摄入的食物等等所塑形。
心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形状,被制约了,而这种制约是一种扭曲。只有当扭曲不存在时,心才能够非常清晰、纯净、完整、纯真地去看。
第一步是看的能力——倾听的艺术——没有扭曲地看,那意味着心必须彻底安静,没有一丝活动。不停活动着的心能否彻底地、绝对地安静下来,没有丝毫运动,也不采用任何方法、体系、练习和控制?心必须清空自己,清空过去的一切,才能变得高度敏感;如果载有过去的重负,它就无法敏感。
只有已经了解了这一切的心,才能提出这个问题。而且,当它提出了这个问题,它也没有答案,因为答案并不存在。心变得高度敏感,因而极其智慧,而智慧并没有答案。智慧本身就是答案。观察者毫无立足之处,因为智慧是至高无上的。于是,心不再追寻,不再渴望更高层次的体验,因而不再掌控。看看这其中的美,先生。它不掌控,因为它是智慧的。它在运转,它在工作。
因而,在智慧的行动本身之中,二元状态消失了。这一切就是冥想。就像开始出现在山顶上的一片云,周围有几片小小的云朵,当它移动起来,就覆盖了整个天空、峡谷、山脉、河流、人类和地球,覆盖了一切。
这就是冥想,因为冥想是对所有生命的关注,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只有此时,心才能彻底寂静,没有丝毫活动——并非在那一刻持续的期间内如此,因为那一刻没有长度,因为它不属于时间。只有当有个经历寂静的观察者说“我希望能够体验更多”时,时间才会存在。所以,那绝对寂静、安止的一刻,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,因为它不属于时间。因此,那彻底的寂然不动超越了所有思想。而那一刻,因永恒而无限。
摆脱了所有扭曲的心灵,是真正的宗教之心,它并不是光顾寺庙的心、阅读圣书的心、重复仪式的心,无论那些仪式看起来多么美妙;
它也不是充满了意象的心,无论那些意象是被强加于其上的,还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。生活与学习是分不开的,这其中有着浩瀚的美。因为,毕竟那就是爱。爱是慈悲,是激情,对一切的激情。
有爱,就没有观察者,没有二元性:爱“我”的“你”和爱“你”的“我”。只有爱,尽管可能是爱一个人,也可能是爱千万人;只有爱。当有爱时,无论你做什么,都不会做错。但是,我们没有爱却试图去做所有的事情——登月,惊人的科学发现——因而事事皆错。
只有当观察者不存在时,爱才会到来。那意味着,当心灵没有把自己划分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时,才会有那种爱的品质。当思想、时间以及对认同和根基的渴望依然存在时,完整的生活就不可能实现。它们妨碍了完整的、整体的生活方式出现。
你听到了这个说法,然后你就会问:“我要如何停止思考呢?”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,不是吗?你知道时间对于学习一门技能、一门语言或者一个技术上的学科是必要的。但你也开始意识到“成为”、从“现在如何”到“应该如何”的这种运动中也包含了时间,而这种时间也许是完全错误的,也许是不真实的。于是你开始质疑。还是你只是说,“我不明白你在讲什么,但我会带走这个说法”?这就是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诚实,就像谦卑一样,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。当一个虚荣的人培养谦卑,那谦卑就是虚荣的一部分。
但谦卑实际上与虚荣、与骄傲毫无关系。那是这样的一种心灵状态:它会说“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如何,让我来探究一下”,而绝不会说“我知道了。”现在,你已经听到了这个事实:所有的时间都是现在。你也许会同意,也许会不同意。这真是一件致命的事情——同意和不同意。
我们为什么要同意或者不同意呢?太阳会从东方升起,这是一个事实,对此你不需要同意或者不同意。所以,我们能不能抛开我们同意不同意的制约,这样我们双方就都能看着事实,于是就没有了同意和不同意的人之间的分裂?这样的话就只剩下如实地看到事情本身。
你可以说,“我没看到”,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你为什么没看到。然而,当我们进入了同意不同意的领域,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会变得支离破碎。
你是一个生意人,你赚了很多很多钱,然后你建了一座寺庙或者捐献给慈善事业。看看这其中的矛盾。
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真正诚实过——不是为了成为别的什么或者领悟别的什么才诚实,而是保持清晰,拥有一种绝对的诚实感,那就是没有任何幻觉。如果你说了谎,那你就是说了谎,你知道这一点,然后你说“我说谎了”,而不把它掩盖起来。当你生气时,你就是生气了,然后你说你生气了。
你不去为它寻找借口、寻找解释,也不试图消除它。如果你想探究更为深刻的事情,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,那么这一点就是绝对必要的。
不要把事实变成概念,而是与事实待在一起——而这需要非常清晰的洞察。我们越是思考一个问题,越是研究、分析、讨论一个问题,这个问题就变得越复杂。
那么有没有可能完整全面地看一个问题呢?怎样才能成为可能?因为在我看来,这是我们的主要困难。我们的问题正在倍增——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,我们的关系也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扰乱。我们怎样才能完整地理解这一切呢?
显然,只有当我们能够将问题看作整体,而不是看成彼此分开的部分,问题才能得到解决。何时才能成为可能呢?
无疑,只有当这些思维过程全部终止,即那些源自“我”、自我,源自传统、限制、偏见、希望和绝望的思维过程全部终止的时候,才会成为可能。
我们能否对自我不作分析,只是如实地去看,将其视作事实,而不是理论,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自我?不是为了消除自我,得到结果,而是看着自我和“我”的行动,不断在行动。我们是否可以凝视着它,不做任何摧毁或鼓励的活动?这就是问题,不是吗?
如果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,“我”以及“我”对权力、地位、权威、延续、自我保存的欲望都不存在的话,那么我们的问题当然就会结束了!一定存在某种不属于思想的觉察,不带谴责或辩解地觉察到自我的活动,仅仅是觉察,就已足够。如果你是为了寻找如何解决问题、为了改变问题、为了得到结果而觉察,那么问题就仍然在自我和“我”的范围内。
只要我们是在寻求结果,不管是通过分析,通过觉察,还是通过不断地对每一种思想进行检验,我们就仍然处在思想的范围内。思想是在“我”、自我等等这些东西的范围内的。只要存在思想的活动,就不会有爱。只要有爱,我们就不会再有那些社会问题。